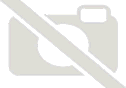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有位網友誠懇地勸我不要再寫詩了,說寫那種東西非得是要有天賦和環境才成,而且現在已經沒誰再有那份讀詩的耐心,她自己從北島、舒婷之後就再沒讀過。我看了不免有幾分慚愧,一是為自己的那些帖子能夠被人抬舉為“詩”,二是我除了著迷於“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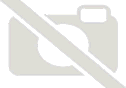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其實小時候我普通話說得特別好,簡直就是一點兒錯都找不著,每回在廣播台錄音時,總編老師也只需翻著字典給我確認一下個別生僻字的讀法,根本就不用糾正我的聲調。當然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,因為我生在北京,並且在我從開始學話到完全長大的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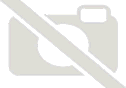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北京城的這種沒有道理的大,讓即使是一直住在這兒的人有時也覺得可怕,從這一邊到那一邊,從這一角到那一角,沒有抄近的斜路,馬路橫平豎直,全得走直角。要是再算上塞車、紅燈、交警的罰單和交通卡上扣掉的分,讓人簡直連想都不願意想啦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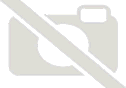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剛參加工作那會兒,有同事被人請客,總愛把我帶上跟著,一是為了手下多幾個人能壯壯門面,再有就是想讓我們這些新手見見世面,學點兒規矩,也順便籠絡一下回去好給人更賣力氣地干活。我呢,當然也特別樂得。其實倒也不是為了那一頓飯,主要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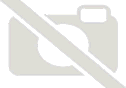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在我和娘收拾南下的行裝時,我爹就囑咐我一定要帶娘去寒山寺看看,在他心裡,那是個最能代表蘇州的地方。我知道爹酷愛古詩文,他對寒山寺的偏愛也許有其親身的感受,但大部分可能還是來自於對那首古詩的印象。當我小得連字還認不了幾個的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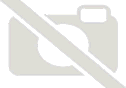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終於到北京了,來之前把網都翻了一遍,真是E游北京啊。於是遵照攜程推薦的北京五日游,開始了北京之旅。首先當然是住的問題要解決啦,住在高校裡很不錯的,環境治安都好,吃的也便宜。就是離市區太遠,還好,從住宿費裡的剩下來的可以用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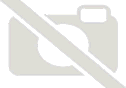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抓髻山實在是一座無名之山了。這一點,從我們在距離抓髻山2公裡的地方向原居民打探都不能得知就更加確定了。抓髻山坐落在北京的西南方向92公裡處,屬門頭溝區雁翅鎮。最近的村莊是一個叫付家台的小山村,約千余人,疏疏撒撒地散落、分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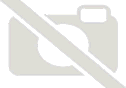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二 司機師傅有四十多歲,門頭溝某地人,以開車拉客為生,兢兢業業本本分分地工作著。因為給我們的價錢便宜而得到同行的質疑,而其一再高聲爭辯說,我這只是為了一個整活兒,不想等在這裡——。 司機師傅一路上給我們介紹了許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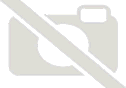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今年不是我們的整年,不管我們怎麼費盡心思翻過來、倒過去地算。母校的風氣歷來務實,推崇低調,不事張揚,多少年難得地大張旗鼓作一回整壽,卻又不是我們這屆的整年。其實就算是整年又能怎樣,有太低的輩份兒擺在那兒,學長前面有的是學長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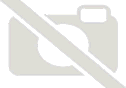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抓髻山實在是一座無名之山了。這一點,從我們在距離抓髻山2公裡的地方向原居民打探都不能得知就更加確定了。抓髻山坐落在北京的西南方向92公裡處,屬門頭溝區雁翅鎮。最近的村莊是一個叫付家台的小山村,約千余人,疏疏撒撒地散落、分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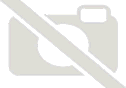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司機師傅有四十多歲,門頭溝某地人,以開車拉客為生,兢兢業業本本分分地工作著。因為給我們的價錢便宜而得到同行的質疑,而其一再高聲爭辯說,我這只是為了一個整活兒,不想等在這裡——。司機師傅一路上給我們介紹了許多有關山的、人的、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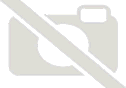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我們乘坐一輛談好價錢的面包車,離開了爨底下村。原本說直接到付家台,去永定河捕魚抓蝦登抓髻山的。但是那個20來歲的司機說不知道抓髻山在什麼地方,並極力推薦一個叫雙龍峽的地方。並一再聲稱那裡是一個新開發的地方,風景棒極了。沿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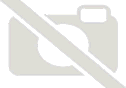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紫荊是我們學校的校花。不知怎麼弄得和香港的市花同名,但我懷疑它們不是同一種花木,因為我的學校在北方,氣候與香港的差異應該很大。香港的市花好象是個六瓣的圖案,能畫出圖案來,想必花應該不小。我們校園裡的紫荊花好象沒誰注意過到底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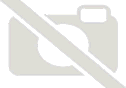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我很感激並且欣賞咱們的頭兒hyzou,為他對我的帖子的關注,也為他的誠懇和幽默。讀他的點評常常會讓我從心裡邊兒往外樂。在這裡我是個應該還算得上守規矩的寫手,只不過常犯些屢教不改的錯。比如上回hyzou忍無可忍地說了我一句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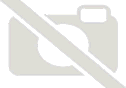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我的同行們為人處事大都很直。在我們那個圈子裡混久了,你就會知道,如果一味地忍辱負重、責已恕人,也許會被懷疑為對所做工作的不能勝任。而如果談吐舉止過於委婉謙虛、優雅含蓄,就別怪自己的意見引不起重視,甚至在很多時候根本就不被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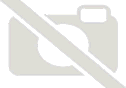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先說北京: 我已是第4次到北京. 然而八達嶺已被弄的不象景點, 且居然不到長城非好漢的石碑被允許建在長城上. 故宮已沒什麼可看了, 就看看建築吧. 大多景點都是如此, 貴了很多, 看的少了. 恭王府尚可, 門票60. 天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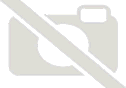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挺有意思的一篇文章,相比上海男人,網上談北京男人的不多.看看吧摘自 多維周刊總第 37 期 北京男人的“嘴”,實在是件利器。和北京爺們兒聊過天兒的都深有感觸。凡事不能一概而論,話雖如此,但現在講究個“概括”、“總結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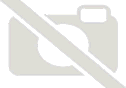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穿過了那片廣闊的平原..京沈公路..那是怎麼樣的臥在路邊的土地啊..眼睛就是直直的望過去..一下就到了天邊..地的邊緣是圓的..墜落了..天接住了地..行車三小時..車速120碼..從沈陽計算..我打了個盹..睜開眼的時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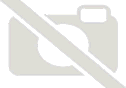
我很想寫一個更惹眼的題目比如“情系北京結”或是“箭扣記行”,我原是奔著那個地名去的,為此不惜顛顛簸簸地在通往黃金冶煉廠的那條土路上跑了那麼久,可一下車,一位當地女人的一句話,就碎了我的夢。就是那個穿著紅馬甲、戴著棒球帽、梳